[内容提要]天津是一个西方宗教派系传入比较纷繁的城市,历史上很多与基督教有关的事件发生在天津,可以说,天津是近代基督教历史的一个见证。本文使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天津基督教会的历史与现状为例,通过几个教堂的兴衰变迁,揭示基督教在天津的发展,并进一步分析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在天津传播现象背后的原因,管窥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路,以期为基督教在中国或者在其他文化中的进一步传播找到一条可行之路。
主题词:基督教,中国,天津,本土化,历史与现状
“本土化”(inculturation)是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所指含义是教会信仰的本位化、本土化、本地化、本国化和本色化,即文化的互融和适应。惟经过一个整合的过程:一则忠于地方教会的本地文化,一则也忠于基督宗教的原始讯息,则本位化的教会才算大功告成。
[③] 鉴于此,本文将主要使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天津的基督教会的历史发展和现状为个案,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参与观察和历史研究等方法,展示基督教在天津的本土化发展,以此来管窥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之路,彰显出汉语神学在天津、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的生长及其所做出的建树,亦以期为基督教在中国或者其他文化中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探索一条可行的道路,也可谓是在宗教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粗浅的尝试。
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时,地处京畿、濒临渤海的天津便首当其冲。1858年,清政府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天津条约》,所有条约中都列有容许外国传教士在内地自由传教的所谓“宽容条款”,肯定基督教的“劝善”性质,规定对传教习教之人皆予“保护”。这在中法《天津条约》中规定得最为详细,并且所体现的法方的教权要求也最高,这是中外不平等条约中明确规定传教士可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开端,也标志着基督教在天津正式开始传播。在保教条款的庇护下,大批的外国传教士涌入了天津。
回望基督教在天津传播和发展的将近150年的历史,是经历了“血与火”的“震撼性”考验,“火烧望海楼”、“义和团运动”、“老西开事件”、1976年唐山大地震对合众会堂等教堂的重大损毁等,不一而足。然而,磨难并未使天津基督教发展停滞,反使之选择并走上了一条适应中国、适应天津的本土化道路,基督教义和天津当地文化的相互作用和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揭示出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可行之路。
基督教三大派别:天主教、东正教、新教,最初传入天津的经历各有不同。1860年天津开埠,最早传入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他们1862年在天津建立第一座基督(新教)教堂,随后英国基督教圣道堂在英租界内建立合众会堂。天主教也同时传入天津,法国遣使会1861年最先进入,而天津市内第一座天主教堂——望海楼教堂的建成则是在1869年。之后,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经历并见证了中国和天津的诸多历史变迁,直至今日,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在天津的宗教中依然占很大比例,对本土文化依然起着重要作用。相对于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传入,东正教的传入更晚一些,1904年,俄国人聚居的地方建立了东正教祈祷所,1909年建成天津最早的东正教堂——救世主堂,即后来的圣母帡幪堂,也是天津东正教的主堂。但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由于东正教来华团本身的目的有获取情报之嫌,也由于俄罗斯本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科技文化的落后,使得东正教在天津的传播很缓慢而且对天津本土的直接影响甚微,现在天津已经没有东正教会。
故此,本文对东正教在天津的发展将不予论述,而只论述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在天津的发展,文中分别选取天津的两个天主教堂和两个基督教(新教)教堂,通过对其历史和现状的比较,分析一些天津基督教现象的可能原因,以期从中展示并揭示基督教本土化的一个可能的进路和发展道路。
一、天津两个天主教堂的历史和现状
这里选取紫竹林教堂和西开教堂,选取它们是因为一定意义上它们代表了天津天主教的发展历程。紫竹林教堂是历史上最有品味的一个教堂,到教堂来参加宗教活动的多是欧美各国侨民,随着中国历史的变迁和自然风雨破坏,如今的紫竹林教堂已经没有了当日的繁华,只剩下一个依稀见出旧日风光的教堂建筑伫立在海河岸边,让世人默默回味昔日的辉煌。西开教堂因“老西开事件”而闻名,它是天主教天津教区总堂所在,历史上的两位外国主教——杜保禄和文贵宾都曾在西开教堂居住生活并主持宗教活动,掌管教区教务。现在西开教堂是天津市区最大的天主教堂,可容纳2000余人,每逢主日,无论刮风下雨,教堂里都会坐满前来参加弥撒的信徒和非信徒。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这两个教堂的排序先后,并非仅仅依照其建造的历史先后,同时也意在按照它们所反映和体现出的本土化程度,由浅而深来阐述。
(一)紫竹林教堂——繁华褪尽终萧瑟
在老天津的教堂中,位于法租界海河岸边的紫竹林教堂应该说是当年“门槛”最高的。当时出入紫竹林教堂的多是有身份地位的外国教徒和中国教徒中很有地位的人,一般教徒很难跻身其中。
对于紫竹林教堂的建造,从有关资料中了解到,火烧望海楼之后,法国传教士对天津民众心有余悸,故利用租界地的特权,把教会的活动中心向租界转移,于1872年在紫竹林寺旧址上建起了新的紫竹林。“紫竹林教堂的造型具有文艺复兴晚期建筑的典型风格,吸收了古希腊、古罗马建筑艺术的积极因素,建筑风格和谐开朗,布局条例次序,不仅雄伟有力,而且活泼轻松,给人以亲切悦目之感。……紫竹林教堂为青砖木结构,再饰以中华的传统砖雕,巍峨典雅。”
[④]由此可见,在紫竹林教堂的建造中,已经开始把中西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加以融合。不可否认,这种做法一定意义上是为了缓和天津民众对“洋教”的愤怒,也在实际上把基督教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因此,这座充满浓郁的异国情调的教堂在此后的很长时间,成为很多侨民和有相当地位的中国教徒参加宗教活动的主要去处。义和团运动中,紫竹林因地处租界而成为很多教徒的避难所;民国前后,这里也是很多外籍教徒和在洋行做事的中国教徒常去的宗教活动场所。
今天的紫竹林教堂静静伫立在一群低矮破旧的砖房民居中间,用自己的异国情调展示着昔日辉煌。当作者采访附近居民,问起紫竹林的过去和现在的时候,他们对此似乎很漠然,当年的繁华已荡然无存,而今的破落和萧瑟是最大的特征,教堂被一些企业用做存储物品、堆放杂物的仓库,而且下雨天常会漏雨。透过大门的缝隙,还能看到教堂里高高的穹顶和宽阔的圣坛,居民们介绍,教堂的唱经楼设计的非常别致,螺旋式的楼梯,上面有当时天津仅有的两架管风琴之一,还有其他的西洋乐器,演奏时,给人以庄严和神圣之感。然而,这些终究已经成为了过去,只是留在了人们的讲述中。我们现在所见的是一幅无可挽回的萧瑟,这恐怕就是教堂失去其生存发展所必须凭依的广大信徒这一基础而致的结果。【见图1,图2】
图1:而今的紫竹林教堂,大门周围已被杂物占用(除合众教堂外,文中图片均为作者所摄)
图2:依稀可见紫竹林教堂的彩色镶嵌玻璃窗,但是现在颜色却已经难以识辨了
(二)西开教堂——风云际会后的辉煌
旧时的西开教堂是天主教会主教的座堂,现在依然。
1912年,天津建立独立教区的时候,罗马教廷任命法国神父杜保禄为首任主教。但早先的天津教案仍让人心有余悸,所以在天津传教中心的选择上经历了数度迁移而最终选择了老西开地区。一则因为望海楼附近地区已经没有了拓展空间,二则老西开地区与法租界相连,可为法租界的扩张确立新的基点,如是,他们开始了在西开购置土地,建造新的主教府和大教堂。
1916年西开教堂建成便成为天主教会的活动中心。围绕西开教堂,修建了主教府、修道院和修女院,并且建造了一座医院和五所学校。教会的这些行为无意中淡化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和差异,开始使彼此融合渗透。1920年天津发生灾情,传教士们筹集来救灾款物发放给灾民们,于是很多灾民来到教堂附近落户谋生。因此,西开教堂不仅成为了天津教区的主教座堂,也成为了教徒们的聚居地,有洋行工作的高级职员,有工商业界的精英,而且随处可见各个修会的神父、修士和修女,充满了浓郁的宗教气息,异域情调和本土文化逐渐交融在了一起而形成为一种新的特质文化。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文化互融的过程中,发生了历史闻名的“老西开事件”。如前所述,法租界当局当年在这里建造教堂的意图之一就是为了吞并老西开这片地方,后来他们往这里派驻巡捕,强迫居民纳税,这些举动激起了天津百姓的愤怒,各界群众联合抵制法国的侵略扩张,这使得法租界陷入了困境。而且,天津各阶层民众积极声援支持,全国各地也纷纷响应支援,半年之后,天津民众胜利,迫使法租界放弃了侵占老西开的企图。
“老西开事件”中,天津民众的成功和胜利,也恰恰在无形中使天主教的发展走上了一条扎实的“本土化”之路,因为,正是凭依着最多数、最广大的本地信众的支持,西开教堂在经历了历史上的种种风云际会之后,才能始终处于这种辉煌的巅峰直至今日。在作者随机采访的许多非基督教信徒中,当问起对天津教堂的了解时,95%以上的都会说起西开教堂,而且很多人所知的也仅仅是西开教堂。这一现象的产生,不排除西开教堂地处今日繁华闹市区这一地理位置的优势,更主要的恐怕也在于西开教堂的发展之中,它选择了一条堪称成功“本土化”道路,把一种异质的宗教文化逐渐融合进本土的文化之中,而将彼此文化的优秀方面展示了出来。【见图3,图4】
图3:西开教堂地处闹市,高耸而醒目 图4:西开教堂内景,辉煌而眩目
二、天津两个基督(新教)教堂的历史和现状
新教是正式传入天津最早的基督教派别,最初到天津来传教的差会主要有英美的五大公会,民国前后又陆续有一些外国的差会来天津,因此,教会多被外国传教士所控制。于是,一些中国基督教人士开始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基督新教教会,成立“自立会”。天津的新教教徒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的建立中国人自立、自传、自养教会的主张,这是一种积极的将基督教本土化的方法,经过了将近百年的实践证明,它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里依然选取两个新教教堂为例,其选取的原因和意义与介绍的排序与前述的天主教基本相似,也期望能从这种不同的教堂的发展变化中折射出新教的发展之路,进而为基督教在天津本土的发展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选择。
(一)合众会堂——不同派系的主动联合
与天主教紫竹林教堂相似的,合众会堂的教徒们也多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文化品位相当高,一般普通信徒难进其中。合众会堂初建于1864年,也是为满足来津的外国信徒进行宗教活动的需求。当时来到天津的士兵、商人和传教士分别属于不同的新教派系,这些分属不同的独立性很强的派系的信徒们,为有一个宗教活动场所,集体捐资建造了最初的合众会堂。显然,这一特殊产物的出现,是和时代与文化背景紧密相关的。当时在天津的教徒们主要的有英美驻津的官员,还有富商,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也有一些医生、律师,以及从事技术性的工程、兵器等方面的专家来到天津,因此,合众会堂成为他们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后来,也有很多在外国洋行工作的华人信徒来这里进行宗教活动。这些都使得合众会堂无形中提高了品位,但是,同时也因此而失去了普通信徒这一大众基础。
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合众会堂被地震损毁严重,后被拆除,于是“合众会堂”成为了历史,只能在历史的记载中看到,现实的形式已经不复存在了。分析其原因,地震的自然损毁是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但是,倘若从主观的角度来讲的话,缺少最普遍的信徒这一重要的生长土壤,似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所在。
(二)山西路教堂——历史变迁的见证
山西路教堂建于1996年,是目前天津最大的新教教堂,也是天津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天津基督教(新教)教务委员会所在地。虽然教堂建成不到10年,但倘若从其前身维斯理堂开始追溯,至今早已有百余年历史。
1872年美国美以美会的传教士来天津创建了维斯理堂,全称“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天津维斯理堂”,此名称中所传达出的就是一种主动将外来宗教本土化的努力。1913年,新的维斯理堂在滨江道建成,依然由美国牧师主持。由美国牧师任主任牧师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32年,该堂有了第一位华人主任牧师刘光庆,以后的主任牧师遂始由华人担任。1958年,天津的基督新教教会将原有的教堂合并为四处,实现联合礼拜,其意在于要在联合中求同存异,以真正实现在基督里的合一,山西路堂的前身维斯理堂当时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此堂更名为滨江道堂,即以地点之名取代其宗派之名,应当说,在这个看似顺理成章的改名中,其实也体现出一种对基督教进行本土化的倾向,对于很多中国信徒来说,宗派的差别意义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教堂更多是同他的坐落方位联系在一起,产生一种神圣的崇敬感。1996年在现在的山西路建成新堂。在山西路教堂的发展历史中,华人做主任牧师、名称的改变等等,都可视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的融合,使当地民众更乐意接受和皈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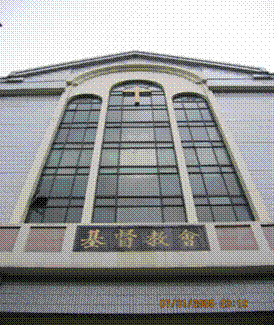
图5:山西路基督教堂外观

山西路教堂的建筑样式也足以体现出一种本土化的力量。不像天主教堂那样有很多样式有规可循,新教的教堂样式都体现出了革新性和多样性。现在的山西路教堂,其主要的大礼拜堂是一个外方内圆的建筑样式,堂内的拱形圆顶由八根柱子往各自的方向伸拉牵引而去,形成了一种规则的八角型体。原来的维斯理堂就是由八根柱子撑起,人们也习惯称呼其为“八角楼”,山西路教堂的建造也是依循了维斯理堂的设计理念,但是又有了很多改造,而成为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八角楼”的样子。
当然,外在建筑样式的新颖,应是源于教会理念的包容性,具体而言就是能对信念各异的人兼收并蓄,因此也在这个过程中见证了天津近代的历史变迁。“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在南开大学学习的时候,为了躲避北洋军阀的迫害,曾经在教堂的地下室进行革命活动,并且还主持了“觉悟社”的会议。1946年,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也来到天津并且应邀到该堂进行讲演。
今天的山西路堂将堂内外的环境都作了改善,八角形的拱顶上悬挂九盏明亮的吊灯,大小礼拜堂可容纳近2000人,是天津最大的新教教堂,每逢主日崇拜会,教堂的过道也会挤满人。山西路教堂为我们展示了基督新教的成功传播,吸引最多数的教友才是重中之重,这样才能使基督教在民族文化中良性地发展起来。【见图5,图6】
三、天津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之综览及原因分析
上述对天津几个天主教和新教教堂的历史发展的描述,只是选取了几个比较典型的“点”来观照,下面将对天津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整体状况做一“面”的比较,主要从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有关数字的比较分析,二是为基督教“本土化”所采取的积极举措,以期能对天津基督教进而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有更为系统的认识和理解。
首先也最明显的是有关数字的统计。本文将循时间顺序,将相关信息加以比较分析。
天津开埠以后,基督教传入天津,从最早的基督新教差会公理会来天津直到1951年,期间进入天津的天主教修会共17个,而基督教(新教)差会则有11个。
从义和团败落到天津解放前夕,天主教在天津共建43座教堂,包括市区的15座和乡村的28座,其神职人员由最初的几十人增至200余人,还开办了大学1所、中学4所、外侨子弟学校2所、职校1所、小学12所和医院救济机构4处,并且创建了北疆博物院(即:现在的天津自然博物馆)。从教会当年的一些资料中,作者发现了一份1903年至1911年天津天主教教徒人数和成人领洗人数的统计表,教徒人数从1903年的3490人增至1911年时的31398人,成年人领洗人数从447人增至6228人,由此可看出天主教影响之大、信徒人数增长之快。
同样在此阶段,基督新教共修建教堂44座,拥有教职人员64人、教徒7000余人。基督教还在天津建立了基督教青年会(1895)、基督教女青年会 (1913)、圣功神学院(1932)、青年归主大会(1945)等团体,开办了10所中、小学校和2所医院以及1家报纸《新生晚报》。
[⑤]
解放以后,政府确定了基督教的合法性,同时实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原则。这都对基督教的本土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之后的基督教发展,很大程度上都是遵循这一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基督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天主教堂自80年代开始相继修复开放,现在全市共有天主教堂21座,其中市区3座,郊县18座,另有临时活动场所和会所20余处,现有30位神父、15名修道生、34名修女,信徒达10余万人。另外,90年代以来,天津天主教于1993年在望海楼教堂成立了备修院,1994年调整充实了修女院,陆续选送修士去全国神哲学院、北京修道院、上海佘山修道院学习,并祝圣了一批年轻神甫,使得神职人员的队伍不断充实壮大起来。至于教区主教,因为原主教石鸿臣主教2005年3月去世,新主教还没有产生,一直空缺至今,但是教会和政府都在积极为此努力。说到10万余人的信徒数,使人不得不感慨于天主教对天津的影响,在市区感受还不那么强烈,但是在郊县农村的有些地方,你可以强烈感受到天主教的影响之大,有些村子全村人都是天主教徒,号称“天主教村”。一位霍教友告诉作者,这样的村子比较于其他的没有这么多信徒的村子来说,管理起来相对容易,家庭和睦,村子里的各项工作都能很好开展起来。
纵观天主教在天津的传播,1866年市区仅有教徒2百余人,1912年成立天津教区,教徒增至2千余人,1926年增至7千余人,1945年增至1.5万余人,建国初期约1.8万余人,至今的教徒达到10万人。而神职人员也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变化而增减,成立天津教区的时候,仅有神职人员数十人,后来逐渐增多,至解放前夕达2百余人,五十年代初开始,外籍传教士陆续返国,神职人员数目减少,改革开放以来,神职人员人数又恢复了增长势头,如表1所示。
表1:1912年——2005年天津天主教神职人员统计
[⑥]
|
年份 |
主教 |
神父 |
修女 |
修士 |
合计 |
|
1912 |
1 |
19 |
37 |
11 |
68 |
|
1930 |
1 |
34 |
70 |
18 |
123 |
|
1940 |
1 |
56 |
125 |
26 |
208 |
|
1949 |
|
79 |
154 |
15 |
249 |
|
1958 |
1(宗座总理) |
42 |
71 |
8 |
122 |
|
1963 |
1 |
45 |
57 |
8 |
111 |
|
1986 |
1 |
19 |
18 |
3 |
41 |
|
2005 |
* |
30 |
34 |
15 |
79 |
(注:*天主教天津教区原任主教于2005年3月去世,时至今日,还没有新主教被晋牧。)
同样,基督新教的发展也基本呈上升趋势。1979年开始,天津基督新教先后修复开放了滨江道(即:现在的山西路堂)、仓门口等教堂。此后,基督新教教堂和活动场所不断增加,现在天津共有基督新教教堂6座,其中市区4座,郊县2座,聚会点190多处,牧师15人、长老3人、传道员3人,教徒近3万人,每年都有1000多人受洗加入教会。在调查过程中,教会为笔者提供了两份统计表,从中也看出天津基督新教的上升趋势来,参见表2、表3中所示的有关统计数字。
表2:天津基督新教教会自建国以来受洗和聚会情况统计表
|
时间范围 |
受洗人数 |
聚会人数 |
|
1949—1983 |
257 |
110—220 |
|
1983—1993 |
2745 |
1100—2200 |
|
1993—2000 |
7570 |
7700 |
|
2000—2005 |
3993 |
8920 |
|
合计 |
14565 |
17830—26870* |
(注:*聚会人数因其无定性,所以教会提供的数字也只是一个约数和估计。)
表3:天津基督新教教会1980-2004年受洗信徒统计表(选取几个年度的数字统计)
|
年度 |
受洗人数 |
弟兄 |
姊妹 |
|
1980 |
6 |
2 |
4 |
|
1985 |
52 |
15 |
37 |
|
1990 |
442 |
74 |
368 |
|
1995 |
801 |
129 |
672 |
|
2000 |
1129 |
286 |
843 |
|
2002 |
1278 |
266 |
1012 |
|
2004 |
1211 |
|
|
|
合计(1980-2004) |
14565 |
2407* |
10259** |
(注:*因为教会统计的只是总人数,还没有具体统计2003、2004年受洗的弟兄人数,故而这里的数字截止2002年;**同*,数字不包括2003、2004受洗的姊妹人数。)
纵观基督教(新教)在天津的传播,教徒人数不断增长,教牧人员的数量不断变化。1870年前后仅有教徒3百余人;义和团运动前夕,五大公会在天津有教徒约2千人,嗣后教徒猛增至4千余人;建国初期有教徒7千余人,1986年底有8千人;现在教徒达到近3万人。教牧人员也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变化而增减。新教刚传入天津时,五大公会的外国传教士仅8人,后来外国差会陆续传入和自立会成立,教牧人员随之增多,解放前后,外国传教士开始相继撤退,教牧人员的数量略有减少的趋势。截至2005年,教牧人员的变化可参见表4所示的有关统计数字。
表4:1862年——2005年天津基督教(新教)教牧人员统计
[⑦]
|
年份 |
外国传教士 |
中国牧师 |
中国传道人 |
合计 |
合计 |
|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
1862 |
4 |
4 |
|
|
|
|
4 |
4 |
8 |
|
1900 |
11 |
13 |
5 |
|
|
3 |
16 |
16 |
32 |
|
1936 |
18 |
20 |
18 |
|
10 |
6 |
46 |
26 |
72 |
|
1945 |
24 |
24 |
20 |
|
16 |
20 |
60 |
44 |
104 |
|
1952 |
2 |
2 |
22 |
1 |
16 |
21 |
40 |
24 |
64 |
|
1958 |
|
|
10 |
2 |
10 |
2 |
20 |
4 |
24 |
|
1986 |
|
|
10 |
1 |
10 |
2 |
20 |
3 |
23 |
|
2005 |
|
|
18* |
3 |
|
21 |
(注:*因为在调查中,教会未能提供详细的男女性别人数,故而只有人数总计。下同。)
综合上述各项比较,天津基督教的发展势头整体呈上升趋势,对于基督教的本土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和生长土壤。当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最初利玛窦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时期的形势已完全不同,利玛窦分析当时情况,“总结了范礼安在日本的亲身经历以及1552年在上川岛故去的方济各·沙勿略的经验,确认……要想改变中国就要从社会的最上层入手。”
[⑧]认为传播基督教首要的是追求信徒的质而不必追求量,即,发展士大夫这一在中国社会中占有重要作用的人群来皈依,这样才能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站住脚、扎下根。今天基督教的发展则是要不断扩大自己在当地民族文化中的分量,因此,关键在于争取民众和信徒来皈依,以提升其影响,这样自然会更利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因此,紫竹林教堂和合众会堂的“高门槛”而至最终的消亡,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就是:没能很好的建立起本土化的基础,失去了普通信众这一重要的生长土壤。相较于它们最终的沉寂,西开教堂和山西路教堂走的是发展广大信众的路线,事实证明这是教会发展所需要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基础。
从上面的比较中也能看到,天津现在的天主教徒人数(10万余人)远远多于基督新教信徒的人数(近3万人),对于差异的造成原因,天主教西开教堂和基督教山西路教堂的两位教内人士给了作者分别的解释。在西开教堂,作者采访了天津市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的一位刘姓教友,他告诉作者,在10万余天主教信徒中,30-40%属于地上教会的信徒,就是进教堂参加仪式的信徒们,60-70%的属于地下教会的信徒,有些地下教会的信徒不进教堂,只在教堂外面虔诚的做仪式,所谓的地上和地下之分,关键在于对“三自会”的不同看法,其他的对天主教的认识、对教义的理解都一样,因此10万余人这个数字就包括了这样的信徒在内。其实,2007年6月30日,罗马教皇本笃十六发表了题为《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的牧函,这也使得地上地下之分有了新的理解。在山西路教堂,一位刘姓牧师告诉作者,基督新教信徒人数是2.6万余人,将近3万人,这些都是在教会中有比较确切的记录和统计的人数,至于家庭教会等等,因为他们的随意性,所以很难有比较确定的统计;而且,天津的基督教(新教)教徒群体相对北京或者其他地方教徒人数忽高忽低的变化更要稳定,也许是天津本土沉稳的文化氛围影响所致。刘牧师进一步解释,天主教徒多于基督新教徒这一现象在中国北方大部方地区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而在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却正好相反,这是因为近代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不同,天主教最初是从北京开始往南方传播,故而北方的信徒为多,基督新教的传播恰恰相反,最早来中国的新教传教士是从广州开始他们的传教活动,由南方往北方传播,因此南方的新教信徒多于北方。
图7:天主教望海楼教堂主日弥撒仪式的教徒
其次,为基督教“本土化”所采取的积极举措。
相对于世界其它地方,在近代中国传教具有相当难度,这种障碍主要体现在中国文化的特质上。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顽强的自我改造能力,因此,一种外来文化要想在中国扎根而又不被本土化就变得非常困难。在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被本土化的命运。天津基督教亦然。
在早年的传播过程中,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比利时人雷鸣远神父提出了传教士要“本土化”的主张,这对天津近代教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02年,在武清传教时,他性格谦和礼让,用汉语和当地人沟通,为与社会名流交往,雷鸣远也尽可能在吃喝住行方面仿效他们,吸水烟袋,留长指甲,梳长辫子,出行坐轿。“老西开事件”后他给罗马教皇写信,为中国的信徒们争取公正决断。抗日战争爆发后,雷鸣远带领修道生们参加了中国抗战,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自己年事已高,长期在战场上救助伤员,终于积劳成疾,后来葬在了中国。他被称为“圣人”、“抗战老人”、“丹心远迈武乡侯”,这彰显出他对“本土化”做出的丰实成果。
基督教对于“本土化”的努力固然见于礼仪改革,推行中文弥撒、用中文经文行圣事,使得广大信徒们不解拉丁文意义的观望,而改变为参与,对弥撒圣事奥迹加深理解。进而视之,在本土化的进程中,很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国情的举措还有基督新教的“联合礼拜”。联合礼拜的实行,是要在联合中求同存异,真正实现在基督中的合一。这其实也是对基督教本身的一些改造,使基督教减少一些对本土文化而言比较繁复的内容,经过这种简化,基督教会更易于被本土大众接受,这也是基督教得以很好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四、结论
通过对天津基督教发展中的“本土化”之描述与分析,可以窥见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之路。本土化这个术语可以用来指称导致基督教与民族文化综合的整个过程,是文化间的积极调和与结合,不是消极地适应某种文化环境。当一种域外文化传至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国家时,在保持其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接受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的改造,从深层找出共同点,吸纳其中可通融的要素,才能在异国他乡求得生存和发展。这就是世界文化交流史的一种规律——本土化。一定意义上来讲,这种本土化现象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原则的体现,因为这种现象群拥有一定的内在统一性。E·特洛尔奇在《基督教理论与现代》中,论及“宗教原则”时提及了“原则”一词的历史哲学意义,原则“被用于每一种由某一确定利益强调的整体,既可以是对个别性格的分析,也可以指对作为个别突出文化阶段或者文化因素的民族性格的分析。……既可以为了表述目的一般地说明一个整体的内容,也可以将这种一般性看成是说明事实上正在发展着的整体本能力量的公式。”
[⑨] 进言之,所谓基督教的本土化,是指基督教与当地民族文化相融合,不断改造自身,以获得传播与发展的过程。虽然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的差异会使二者发生激烈的冲突,但这些障碍是可以克服的。基督教在与本土文化调和方面充分显示出了它的柔韧。中国的神学应该从中国的文化社会历史中找寻资料。正如段琦在《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一书的序中所提到的,“对于‘本色化’(即本文中所说的‘本土化’——本文作者注)这个名词的理解,教会人士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理解,但大家都承认一个不争的事实:一种外来宗教要在某地生根,必须与当地的社会与文化相适应,否则必然被淘汰;对于中国基督教来说,‘本色化’就是跟随时代,调整自己,以适应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客观现实。”
[⑩]进而,我们也应清醒意识到,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为基督教对其文化环境的单向适应,而应视为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相互作用、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承认基督教本身也具有文化创造力,那么,当我们充分认识到基督教和本土化都是开放的、包容的过程时,这二者才能真正实现最佳的融合,以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惟其如此,在天津、在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大地上,汉语神学方可真正产生出其独特的建树来,对我们的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文章资料的收集整理过程中,作者走访了天津市宗教局有关领导,还有教会的牧师、神父和义工、同工以及“两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教务委员会)的有关负责人等,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宗教终究是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对很多方面不能完全放手不管也不能政府全管,这就必然使得在对宗教的管理和控制上,教会和政府还有些方面需要磨合来调节,才能使基督教与天津文化更加融合来促使彼此的进步。当然,从天津基督教的历史和现状来看,我们已经看到本土化的成功,然而,宗教与本土文化的完美融合,还需要更长时间做更多的实践才能真正实现,这是本土文化和神学都需要努力来做的。
______________
参考文献:
1.段琦,奋进的历程 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E·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基督教理论与现代[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3.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天津简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4.天津市档案馆主编,于学蕴,刘琳编,天津老教堂[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5.约瑟夫·希波斯(Joseph Sebes),《利玛窦对“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的努力》[A],林治平编著,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93—107页。
注释:
[①] 文中“基督教”指的是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其三大派别,即: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现在我们通常讲的“基督教”在文中称为“基督教(新教)”或“新教”。
[③] 参见 http://www.21music.org/NEW/BLESSING/dict/I.htm
[④] 于学蕴,刘琳编著,天津老教堂[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11-12页。
[⑤] 以上有关数字主要根据天津市档案馆馆藏的调查表统计而来,调查时间是1951年。
[⑥] 部分参见: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天津简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第1254页。因为近年来基督教在天津的发展比较稳定,所以本文的有关数据统计均截止到2005年12月。
[⑦] 部分参见: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天津简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第1260页。
[⑧] Joseph Sebes著,《利玛窦对“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的努力》[A],林治平编著,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C],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第96页。
[⑨] E·特洛尔奇,基督教理论与现代[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第171-2页。
[⑩] 段琦,奋进的历程 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序》第2页。
(作者系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
(本文是作者在2008年北大宗教高峰论坛上的发言,感谢作者和会议主办者授权本网首发。)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