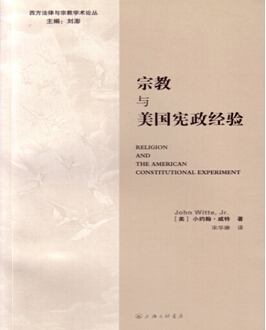
良心自由同宗教的自由实践联系在一起。良心自由是不受干扰的选择、接受和改变个人宗教信仰的权利。宗教的自由实践是一旦根据良知进行了选择,即可据此公开行事的权利,但要以不侵犯他人权利和社会的整体安宁为限。在宗教良知和宗教实践之间的如是有机联系是为西方传统所周知的,在英美作者的著述中也没有失却。在1670年,教友派领袖威廉斯·佩恩就将这两类保障联系起来,坚持从“从平易的英语”出发,宗教自由所限定的“不仅是信或不信的心智自由,”同样还有“我们良知的自由实践且不受干扰,就礼拜仪式而言,我们得到了清楚地劝告,上帝要求我们为他服务。”在下一个世纪,这种有机的连接变得十分平常。麦迪逊写到,宗教“必须留给每个人的信念和良知,按照自己信念和良知的支配进行宗教实践,是每个人的权利。”因为宗教包含了“我们对造物主的义务,以及履行这些义务的方式。”对大多数18世纪的著述者来说,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是相互关联的,两者都应受到法律保护。
尽管18世纪的著述者们和词典上都没有为“自由实践”给出一个定义,这个短语通常隐含着包括宗教礼拜、宗教言论、宗教集会、宗教出版、宗教教育等多种公共宗教活动形式在内的实践自由。它还意味着参加宗教辩论、宗教发展以及传教活动的权利。但必须是和平地行使,如纽约律师亨利·利文斯顿(Henry Livingston)指出的:“我坚信,去维护基督教是一回事,向信仰不同的人去灌输信仰,是另一回事。”
宗教自由实践还乐于去承认,个人有权利参加由类似信仰者组成的宗教团体。跟我们今天一样,信教个人可以自由地修正自己的礼拜模式、信仰物事、教规戒律和/或宗教礼仪。建国者并没有象今天一样去提及“宗教团体的权利”或“法人的自由实践权利”。但是他们的确提及了“教会自由”、“一个教派和另一个教派之间的……平等自由”,以及“纯宗教权力的完全享有和自由实践……这可以是同社会的公民权利相一致的。”
每个早期的州宪都对某种类型的“自由实践权利”予以保障,所经常增加的限定是,这样的实践以不能侵害公共和平或他人的私人权利为限。大多数州将此保障限于“宗教礼拜的自由实践”或“公开宣称宗教信仰的自由实践”——因此如果有其他宪法条款的话,就留给其他宪法条款,来对除礼拜之外的其他宗教表达和行为形式加以保护。有些州规定了对自由实践的更为一般化保障。例如,弗吉尼亚州宪法保障“根据良知支配的宗教自由实践”——因此那些宗教的和非宗教的表达和行为,只要是为良知所支配的,就可延伸适用自由实践的保护。乔治亚州宪法给出了更为确定性的规定:“无论怎样,只要不危及和平和政府安全,所有人都应有从事其宗教实践的自由。”第一修正案的拟定者也选择了较具开放性的表述——“‘宗教’的自由实践”,而没有像一些州那样,去对可能保护的宗教实践类型加以界定或限制,同时它还对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加以保障。
(本文摘自小约翰·威特著,宋华琳译:《宗教与美国宪政经验》,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8-60页。本书为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策划的“西方法律与宗教学术论丛”之一。)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