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有两大教会,它们在规模与重要性方面旗鼓相当。德国的总人口约为8250万,其中天主教约有2650万教徒,而新教约有2620万教徒。新教包括很多分立的地方性教会,每个教会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它们共同构成了德国的福音派教会。与此同时,还有很多规模较小的新教教会,因为选择留在这种联盟体制之外,人们称之为自由教会。新教教会是信义宗或者归正宗,有些教会经由不同的方式从这两种宗教的教义中发展出统一的信条。德国的伊斯兰教大约有320万教徒,犹太社团有10万余教徒,东正教会大约有120万教徒。同时,德国还有许多较小的宗教,有些历史悠久,有些则刚成立不久。它们的教徒数量估计有160万人。另外,据估计,有2200万德国居民声称自己没有任何信仰。
[1]这部分数据(尽管不完全)源于德国的统一,因为前东德的政治体制对教会采取了一种敌视立场。除此之外,由于德国的移民和其他社会变迁,使得民众的宗教信仰观念发生剧烈变化,因此,这些估计数字仍不确定。
二、历史背景
德国的宗教状况甚至在当今都仍受到1517年宗教改革的强烈影响。路德的宗教改革与疆域性的主权以及地方王权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如今的地方性教会,因为这些教会的最高主教经常是地方的统治者本人。王权与神权之间发展出相当紧密的关系,并一直持续到1919年。中世纪以来,天主教会就已经取得相当多直接的世俗主权和权力。特里尔、科隆和美因茨的大主教本身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就世俗权力而言,他们与其他的选帝侯没有什么不同。
1803年帝国代表联席会议后,这些统治者失去了他们的地位。“莱茵河左岸”输给了法国之后,依照1801年的《吕内维尔和约》,“莱茵河右岸”贵族多数对莱茵河左岸的损失进行一定形式的补偿。在此过程中,教会王国的世俗权力被废除,他们大部分领土也进行了重新分配。天主教会的财产绝大多数是世俗化的。因此,和天主教会相比,教区拥有更多的财产。
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承认了信义与天主教具有同等地位。1618年至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之时,这两大宗教派别就不分伯仲。直至今日,宗教团体的地域划分仍继续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
整个19世纪,国家与新教教会之间的纽带都在逐渐松懈。1919年《魏玛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尽管也承认并允许国家与教会在某些事务上进行合作,如公立学校的宗教课程、教会税收和军队专职随军牧师方面。由于德国认识到纳粹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杀戮欧洲几百万犹太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因而赋予犹太人的宗教团体(尽管数量上仍较少)相当可观的社会地位。
三、法律渊源
《基本法》第4条保障宗教自由,信仰与良心自由,以及(宗教或意识形态)信条自由是不可侵犯的。法律保障宗教活动不受妨碍。
保障宗教自由的个人权利在《基本法》第140条得以补充和阐明。这些规范条款实际上是把1919年8月11日《魏玛宪法》中的136条至139条-141条写进了《基本法》,因而它们是非常完善的宪法权利。而且,《基本法》第7条第2款和第3款保障公立学校宗教教育的自由。在基本法和联邦各州的法律中也有很多其它规范,如公立大学应设有神学系。德国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归于联邦各州的职权范围。就教会-国家体制的宪法基础而言,其具体的制度安排确立在基本法位阶以下的法律条款的诸多规定之中。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及其联邦各州与德国的教会签订了很多政教协议与教会—国家条约。
[2]就与天主教教会的关系而言,1933年的《帝国宗教协定》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它被承认为一个国际法条约。与福音派教会的宗教-国家条约以及那些与天主教教区的条约,尽管是特定类型的,但从范畴上讲类似于国际条约。条约或协定也存在于各种更小的宗教组织之内。这样的教会-国家条约,其主题内容包括国家与主教之间的合作、公立学校宗教教育的保障与安排、神学系和随军专职牧师的设置,以及教会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如对宗教堂区的财政支持)。
四、政教体制的基本类属
在欧洲的教会-国家体制之下,德国采取了一种折衷路线,介于国教与严格的政教分离之间。《基本法》确立的是一个教会与国家分离的体制,然而与此同时,它也从宪法上确保两种制度之间的合作形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协同关照民众之需求。德国国家-教会体制的法律基础是围绕着中立、宽容与平等这三个基本原则而建构的。
中立原则要求国家不能认同教会,即不得设有国教(《魏玛宪法》第137条第1款及与之相关联的《基本法》第140条)。
[3]国家不允许对某个特定的宗教组织有任何特别的偏向,或者对这样的宗教组织的特定价值或意识形态作出真伪判断。意识形态机构与宗教机构具有同等地位,这适用于那些有人文主义意识形态或立场,但却没有涉及上帝或神祗问题的组织机构。然而,这仅具有轻微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不得把宗教机构置于比社会组织更不利的地位,这要求禁止做出支持国家无神论的决定。因此,中立原则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不干预:禁止国家在宗教团体的事务中采取决定性行动。这一点在《魏玛宪法》第137条第3款中表现得特别清楚:一切宗教团体在基本法律框架下独立地规范和管理自己的事务。无论宗教组织的法律地位如何,这种自决权都是有效的。
宽容原则要求国家不仅要毫无偏袒地对待所有不同的宗教观,而且要维系一种积极的宽容氛围,以便为社会的宗教需求创造空间。
最后,平等原则要求国家平等地对待所有宗教团体。这意味着,根据宗教团体在宪法上的法律地位差别,需要一种分级对等形式,由此为处理各种社会现象提供充分的基础。这种对待形式是以具体的、团体导向的方式来形成平等对待观念,从历史根源上看,平等对待观念源于宗教信仰的平等——它是16世纪和17世纪宗教战争的后果。
《基本法》第4条有关宗教自由的阐述也体现了这些基本原则。正是在此,我们可以发现积极宽容的要求。保障信仰自由就是为了给每个人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的权利。信仰自由也有消极的方面,即有不拥有任何信条的权利和/或不归属于某个特定的宗教信仰的权利。宗教自由同时也保障个体按自己的信仰行动的权利。其结果是,真诚的信仰在刑事案件中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比如,一个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得了重病,但因为她的信仰而拒绝就医。她的丈夫因为有同样的信仰而尊重她的意愿,结果这位妇女死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否决她丈夫因未尽帮助义务而应负的罪刑,因为在此情况下他没有责任。因此,那些违反法律的人如果真正按照自己的信仰和良心行动,可能就不会产生刑事责任。
[4]
积极宽容意义上的信仰自由也就允许了这样的可能性:只要学生参与宗教活动符合社会态度,并且这种参与完全是自愿的,国家就应为公立学校进行的跨教派祷告提供便利。国家必须确保提供一种宽容的氛围。在国家控制了个人的外部环境的情况下(如规定何时应入学),这时就要求国家为处于此种情境中人的宗教需求提供便利。
[5]这同样适用于国防军和刑罚机构。
宗教机构也享有信仰自由,这种自由作为一种集体性权利而存在。
五、宗教团体的法律地位
在德国,无论信徒众多的宗教团体还是数量可观的更小规模的宗教团体,它们都具有公法法人地位。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中,堂区、教区、地方教会和教会联盟皆被视为公法法人。不像其他公法法人,具有这种法律地位的宗教团体没有被整合进国家结构之中。作为公法法人,它们仍保留完全的独立性。依据法律,教会与国家之间没有特定的认同。政府认为,因为不存在这种认同,所以宗教团体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仅有一些特定的权利与此种法律地位有关。每个宗教团体在向负有职责的联邦州政府提出申请后,只要能通过它们的社团规章和成员人数证明它们确实是一个永久团体,就都能获得公法法人地位(《魏玛宪法》第137条第2款;《基本法》第140条)。在耶和华见证人努力争取成为公法法人时,联邦宪法法院曾明确表示,忠于法律也是获此法人地位的一个条件。2004年时耶和华见证会在行政法院的案件仍悬而未决。
其他一些宗教团体经由民法而获得它们的法律资格。其地位最起码是注册的私人社团。由于要保障信仰自由,因而必须考虑到宗教的独特性。必要时,可以调整民法上的条件以满足宗教上的要求。
[6]正因为如此,联邦宪法法院把宗教自由看作宪法上的要求,当地一个巴哈伊教的心灵劝导会申请法律身份时,法院背离民法上的一般性要求,裁决它应获准注册为社团,即使人们认为心灵劝导会并不独立于巴哈伊宗教运动的其他机构。
六、宗教团体的意义与自决权
教会的自决权不限于与“教会”有关的具体活动这样狭窄的领域。宗教活动自由的观念可以作进一步扩展:教会也在为了达到宗教目标的其它领域保留着自决权,比如开办医院、幼儿园、养老院和私立学校、大学。
德国的大教会,特别是天主教的明爱会(the Caritas of the Catholic Church)和福音派教会的救济会(the Diaconical Works of the Evangelical Church)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服务。如果少了这些社会服务,《基本法》第20条第1款和第28条第1款所承诺的社会国家仅成空谈。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宗教团体和教会真正实现其意义的一部分。在国家法律看来,教会提供的服务也是一个整体。因此,自决权不只从属于作为独特实体的教会本身,它同样属于所有的以此种或彼种方式与教会关联的机构,不管这些关联采取何种法律形式。只要这些机构根据它们的自我认同,认为其目标或义务圆满实现,并且是教会真正的授权,那么,这些机构确实存有自决权。
[8]
正因为考虑到公法法人的地位,因而联邦宪法法院认为教会医院不适用破产法,即便根据医院的章程,这些医院与某些特定的组织化教会之间仅具有松散的联系。如若法院任命的破产事务官在宗教机构的结构或组织中履行公务,那么这将有悖于自决权的观念。
[9]
自决权框架为宗教团体提供的空间被德国的大教会加以利用,制定出周密繁多的内部法规体系,这些法规与国家法处于同一层次,有其自身的特色,并突出了教会的工作重点。在自决权框架内,还有一个属于教会的司法管辖制度。就自决权的适用而言,教会的管辖权只针对教会自身事务和那些不需要公共法庭审查而可内部解决的教会事务。然而,具体说来仍有诸多可争议之处。最新的进展表明,法院越来越倾向于干预教会事务,但他们在评估具体个案时仍给予自决权以相当大的空间。
七、教会与文化
德国的大教会运营着相当多的私立学校。大多数私立学校正在取代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教育水准不亚于公立学校。于是,这些私立学校也受到适用于公立学校的那些重要规范的约束。德国整个教育体系都建立在《基本法》第7条第1款之上,因此所有学校也受国家监管。相对于公立学校的数量,教会或其他私立学校和教育机构居少。在私立学校的财政上,教会像其他创办学校的组织一样能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大的教会为4至7岁的儿童创立了数量可观的幼儿园。
根据《基本法》第7条第3款之规定,公立学校(非教会学校除外)的宗教课是基本科目。尽管国家有督察权,但宗教教育仍是按照宗教团体的基本准则进行。教师没有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进行宗教教学的义务。孩子的父母或监护人有权决定是否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宗教教育。原则上,当小孩达到12周岁时,父母的决定就不能有悖于孩子的意愿。孩子14岁时便能自己决定是否接受宗教教育。根据《基本法》第7条第3款的要求,宗教课是公立学校的基本科目,因而不能把它变成辅修或选修科目。宗教教育的内容由相关宗教的教派教义决定。一旦同一教派的学生达到最低人数,通常是6到8名学生,公立学校就有义务提供相应的宗教教育。宗教团体、孩子以及家长都享有关于此种教育服务的宪法权利。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那就是穆斯林学校孩子的宗教教育问题。尽管这种宗教教育是一项基本权利,但对此服务的诉求却因为缺少伊斯兰团体的出面而屡遭挫败。穆斯林的宗教和文化教育通常在教授土耳其和波斯语的语言文化课上进行,这些课程是为那些移民孩子准备的。在德国的中小学校中,穆斯林学生超过60万。公立学校允许学生佩戴像穆斯林头巾之类的宗教象征饰物。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大多数联邦州中的教师。然而,有些州开始不同程度地禁止公立学校的教师在上课时显露宗教象征物。这个极富争议的议题主要(尽管不完全是)与穆斯林妇女的头巾有关。
德国很多公立大学都设有某一教派的神学系。在诸多不同形式的政教协定中,教会或多或少对大学教授的任命和课程以及考核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方面,天主教教会比福音派教会的控制力更强。国立大学神学系的教授是国家官员,然而,要成为大学天主教系的教授需要天主教会的正式差遣。如若差遣被撤回,那这位教授则不能继续成为神学系的教员。但是他或她仍可以保留作为国家官员的权利和义务,因而必须给他或她在大学另谋一个职位。对于神学教授席位的空缺,国家有义务找到必要的替补人选。
而且,大教会也有自己的神学系。天主教会在艾希施泰特有它的大学,此所大学包括了相当多的非神学院系。另外还有大量的教会创办的学院,相较于大学,它们提供的教育具有更鲜明的职业导向。
教会负有特定的公共使命,这也是它们的一个特殊之处。各种政教条约保障了公共使命的存在,教会的宗教自由则奠定了这种公共使命的根基。因此,这赋予了教会在公共生活上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正是基于它们的公共使命,宗教机构在电视广播中有特定的演播时间段。由此,当需要社会代表发言时,教会可以代表公共机构监事会陈述其立场。德国公共电视一台(简称ARD)、二台(简称ZDF)和地方性广播公司的广播委员会,私人电台的监督委员会,还有负责甄别和限制那些被认为有害于年轻观众和听众的剧本及影视的评估与分级委员会,它们的观点都与教会的立场休戚相关。鉴于犹太社团的历史与文化影响,它们通常在以上这些机构中都有代表。至于穆斯林群体是否以及如何可能在这些机构中产生代表,我们可以对未来的发展拭目以待。
八、教会里的劳动法
德国大教会的雇员人数加起来超过百万之众,由此看出,大教会的雇主地位十分重要。
作为公法人,教会有权设立公共职位。这意味着教会雇员可以被认为是公务员;相应地,教会的行政机构和类似的国家行政机构以相同的方式被建构起来。国家有公务员法,教会也有自己的公务员法,甚至在公务员的薪水和福利方面也有类似的规定。就神甫和牧师而言,有一部独立生效的劳务法,这部劳务法尽最大可能地反映了公务员法,同时也考虑到了教会这种特殊背景。
然而,服务于教会的绝大多数雇员适用的是普通的劳动法。当然,根据教会的自决权及其特殊的宗教背景,在很多情境下也可对劳动法进行修正。宗教自由要求我们在评估这些雇员的劳动地位时,必须考虑到出于教会义务而产生的特殊境况。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教会雇员对他们的教会雇主负有忠诚的义务。在公共秩序、诚信和禁止歧视观念的宪法框架内,正是教会决定了这些义务的内容。宗教团体的自决权允许教会在一般法律的范围内根据自身情况来规范教会的工作条件,确定教会员工的具体义务。教会的哪些基本义务是重要的劳动条款?这需要根据组织化教会自身承认的标准来判断。由于《基本法》承认教会有对内决定事务之权,所以当评估忠诚的契约义务时,如果发生争议,劳动法庭就得尊重教会的标准。这通常交由组织化的教会来决定:何为教会及其教义的要求、何为具体的教会义务、何为信仰和道德的根本原则以及何种情况违反了这些规范。如果雇员违反了这样的忠诚义务,劳动法庭将作出终局审判,由它来决定终止教会雇员的劳动关系是否正当。
[10]教会有它特定的宗教诫命,因此,当教会雇员的生活方式或其公开表达的意见与教会信条相佐时,教会有权对雇员发出解雇通知。联邦宪法法院曾经作出判决,认定对受雇于一家天主教医院的外科医生发出终止劳动关系的通知是合宪的,因为这位医生在电视和杂志上公开反对教会在妇女堕胎权上的立场。欧洲人权委员会维持了这一判决。
[11]
在集体劳动权利方面,教会也因宗教自由观念和随之而来的自决权而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教会的结构不受《共同决定法》(co-determination laws)的限制。
[12]国家原则上不允许干预教会的内部组织结构和机构设置。
[13]教会在此发展出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它们把自身的职业(特别是慈善)理解成心无旁鹜且以宗教为基础的天职。对他们而言,原则上不可能接受建立在劳资根本对立观念上的劳动关系法律结构。天主教会以及大多数新教教会因而会拒绝通过与工会的谈判而达成的协议。
[14]在教会结构中,不存在罢工的权利,正如不可能通过教会内部决定而开除员工一样。教会创设了自己的员工代表和共同决定制度。相较于共同决定制,教会的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员工更广泛的权利。
九、教会的财务
由于过去教会的财产受到不断的侵占,德国的教会现在仅剩一小部分财产。为了补偿1803年帝国代表联席会议以来世俗化进程造成的损害,德国政府作出一系列决定,确保对教会的财政支持。与《基本法》第140条相关联的《魏玛宪法》第138条第1款有如此之规定。此条把这些拨款视为补偿性的给付,还规划了这种给付的终止。由于缺乏现实性,到目前为止这项措施还未得以落实。除此之外,国家给予的其他补贴常常与教会诉求的理由是否充分有关。比如,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地政府有维护教会建筑的公共义务。同样,基于合同条款,国家需要对教会履行一些必要的义务,如补贴教会官员的薪水。
教会整个预算的80%左右都由教会税来负担。《魏玛宪法》第137条第6款和《基本法》第140条皆确保此点。根据民事税收列表和州法之规定,宗教团体是公法法人,允许其征税。不但大教会充分运用这种机会进行征税,具有公法法人地位的小型宗教团体,如犹太社团也都这么做。只有那些被授权可以征收教会税的教会,其成员才有义务纳税。教会税作为一种制度始于19世纪之初,由于当时教会财产已经世俗化,设立教会税是为了减轻国家对教会的义务所带来的财政预算负担。
人若想要免税,只有离开教会才有可能。经相关国家官员的除名,脱离教会便能生效。根据国家的分级体系,这意味着此人正式结束了作为某个教会的成员身份。大多数新教教会把脱离行为也看成退出某个教会,而原则上讲,天主教会把脱离行为看成个人对教会义务的严重违反,但不会引起教会成员身份的神学问题。
教会税的税率在个人所得税的8%和9%之间,但也可能使用其他税收标准。大多数情况下,大教会的税由国家税务局代为征收,尽管这只是与国家达成的一种制度安排而非一项强制性要求。对于这项服务,教会需要向国家支付教会税的3%-5%作为补偿。如果教会成员拒绝纳税,国家可以使用各种法律手段来征税,而教会在其成员不纳税时则不能采取法律行动。由于教会税与教会雇员的收入税密切相关,雇主可以直接把教会税和个人所得税一起提供给财政机关。
由于与国家税的关系,免税也影响到教会的教会税。据估计,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教会成员不需要交纳教会税,因为他们免交个人所得税。有时教会也通过一些方式来改善这种局面,如在个人所得税外要求成员对教会进行一种替代性捐助。
对某些教会机构而言,获得收入的另外一个重要方式是进入公共的财政体系内部。教会经营的医院在德国一些地方成为医院可用床位的主体,因此这些医院成为公共财政体系的一部分,根据病床的占用数而从医疗保险中获得资金,主要以此来维持运作。而且,很多教会也会接到国家委派的活动,其方式与其他公共财政资助的活动一样:这体现了国家中立性的观念,教会活动不应被置于比国家资助的活动(比如说当地体育俱乐部)更糟的境地。
教会也享受一定数量的免税。教会税和教会的慈善捐赠可以从所得税中扣除,这同样适用于对非营利组织的捐赠。教会也免于交纳某些税以及关税。
十、公共机构中的宗教协助
由于在军队、医院、刑法机构或其他公共机构有宗教服务和宗教协助之需要,因而允许各种宗教机构从事这样的活动。他们有权在医院进行以及给予犯人宗教协助。在警察和军队中从事宗教活动由合同加以规范。军牧由教会派送,并提供一定时间的服务。在服务期间,他们具有国家官员的地位,当然也可能是一种合同上的地位。就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而言,他们的最高上司是联邦国防部的首长。德国的军随军牧师是没有制服和军衔的国家公务员。在军队中,为新教牧师设有福音派教会的办公室,为天主教则设有主教办公室,是国家行政体系的一部分。这些职责是教会和国家行政的应有部分。在教会事务上,这些随军牧师代表教会并服从于各自军队中的主教,而在公共行政事务上则服从于联邦国防部长。
十一、牧师和修会成员的法律地位
一般而言,在德国法体系中,神甫、牧师和宗教修会成员在国家法律并没有特别的地位。只在很少情况下才有特别的考量。比如,联邦宪法法院认定如下情况是合宪的:宗教机构可以反对他们的宗教官员在任职期间出任政府公职。
[15]根据德国法律,宗教人士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不受法律限制,也不能设置任何法律障碍。所以,宗教机构对其官员的规制不符合《基本法》第3条第3款,即任何人不能因为其信仰而受到不利或有利对待。而且,《基本法》第33条第3款规定,民事权利之享有、履任公职和在公务中获取之权利独立于个人的信仰。任何人不能因为其信仰或意识形态而受到不利对待。相似的规定也可见于《魏玛宪法》第138条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法》第140条。然而,这种禁止歧视不适用于宗教职位之任用。被委以圣职的新教牧师和被罗马天主教任命的执事皆可以免除在军队履职,其他教派的全职牧师也是如此。接到这样的任命后,这些人可以推延他们在军队的履职。牧师(特别在法庭上)无需为他们担任牧师期间所获悉的事宜提供证词。
十二、婚姻与家庭法
与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相反,德国教会对婚姻和家庭法领域没有管辖权。根据德国法律,婚姻完全是民事问题,在登记机关登记才有效力。其他形式的婚姻,特别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宗教婚姻,只能发生在外国人之间,而且需要两人在他们母国有婚姻管理权的机构签订此种婚姻合约。对德国国民而言,宗教婚姻没有民事效力。尽管如此,所有人都可以享有宗教婚礼仪式之自由。有一条在宪法上可疑的规则规定,宗教婚礼不能先于民事婚姻。然而,违反此条规则并不会受到制裁。
十三、宗教与刑法
宗教在德国刑法和诉讼法上享有相当多的保护。根据《刑法典》第130条第2款,以特定方式煽动仇恨宗教团体者,处以三年监禁或罚金。诋毁宗教或哲学信念以致于扰乱公共秩序者,同样可加以处罚。妨碍德国境内宗教团体的礼拜活动,或在宗教团体进行礼拜的地点辱骂搅扰者也要受到处罚。哲学或非宗教团体的仪式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妨碍葬礼和扰乱死者安宁者一样要受到处罚(《刑法典》第166条-168条)。
未经授权使用公法上宗教团体的名称、级别、制服或旌旗者,处以一年监禁或罚金。损坏或扣压公法上宗教团体的官方文件者,处以二年监禁或罚金;情节严重者,可处以五年监禁(《刑法典》第132和133条)。
告解秘密受广泛保护。任何情况下不得强迫神职人员告知他们在灵性照护中所获知的内容(《刑法典》第139条第2款、《刑事诉讼法》第53条和《民事诉讼法》第383条)。在此种情形下,也不得强迫他们告知蓄谋中的犯罪(《刑法典》第139条第2款)。
十四、教会民事法律问题
过去50年,由于联邦宪法法院(大多很明智的)判例法的发展,德国的国家-教会法律已经有了相当清晰和牢固的结构基础,能以较为妥当的方式回应社会需求。后续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包括承认新的宗教和非宗教团体,特别是伊斯兰团体,另一方面也须考虑到普遍存在的宗教怀疑派。总之,未来任重而道远。
十五、参考文献
Axel Frhr. Von Campenhausen,Staatskirchenrecht,3rd ed.,1983.
Alexander Hollerbach,Grundlagen des Staatskirchenrechts,in Josef Isensee/Paul Kirchhof ed.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vol.VI,1989,p.471.
Alexander Hollerbach,Der verfassungsrechtliche Schutz kirchlicher Organisation,ibid,p.577.
Alexander Hollerbach,Freiheit kirchlichen Wirkens,ibid.,p.595.
Alex Frhr. Von Campenhausen,Religionsfreiheit,ibid.,p.369.
Bernd Jeand Heur/Stefan Korioth,Grundzüge des Staatskirchenrechts,Stuttgart 2000.
Jörg Winter,Staatskirchen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ine Einführung mit
kirchenrechtlichen Exkursen, Neuwied 2001.
Joseph Listl,Das Verhältnis von Kirche und Staat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in
Joseph Listl/Hubert Müller/Heribert Schmitz ed.,Handbuch des katholischen Kirchenrechts,
1983,p.1050.
Joseph Listl ed.,Konkordate und Kirchenverträge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2 vols.,
1987.
Joseph Listl/Dietrich Pirson,Handbuch des Staatskirchen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
land,2 vols.,2. ed.1994.
Gerhard Robbers,Das Verhätnis von Staat und kirche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in
Gottfried Zieger ed.,Die Rechtstellung der Kirchen im geteilten Deutschland,1989,p.7.
西方法律与宗教学术论丛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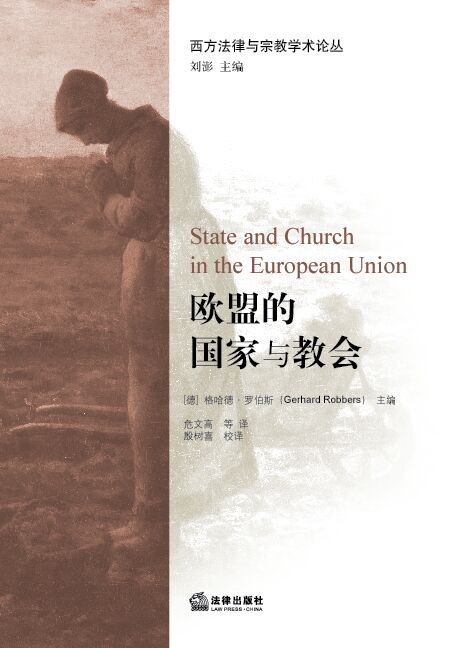
[2] Cf. Joseph Listl ed.,
Konkordate und Kirchenverträge in der Bundersrepublik Deutschland,2 vols.,1987.
[3] 也可参见《魏玛宪法》第136条,它与《基本法》第140条、第4条和第33条的第4款相关联。
[5] Cf. BVerfGE 52,p.223.
[6] Cf. BVerfGE 83,p.341.
[7] Cf. BVerfGE 42,312/334;66,1/20.
[8] Cf. BVerfGE 70,138/162.
[10] Cf. BVerfGE 70,p.138.
[11] Cf. BVerfGE 70,p.138;EKMR,12242/86,1989年9月6日的裁决。
[12] §118 BetrVerfG;§1 IV MitbestG.
[13] Cf. BVerfGE 53,p.366/400.
[14] 然而有些新教的地方教会(如诺德宾和柏林-勃兰登堡教区)与其雇员达成了集体性的谈判协议。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