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奥库涅夫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当中,无论是“顶尊人像”,还是其他艺术图像,均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二者的相似性不是偶然的,很有可能是由于公元前第三、二千纪之交,在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扩散的背景下,以奥库涅夫文化为代表的南西伯利亚诸考古学文化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奥库涅夫文化艺术通过后石家河文化,在三星堆文化艺术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
奥库涅夫文化是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早期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向以发达的石雕艺术闻名[1],并因艺术图像与中国龙山时代及青铜时代诸考古学文化艺术图像存在较大的相似性而备受瞩目[2]。本文将以“顶尊人像”为主,分析奥库涅夫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艺术的相似性,并讨论这种相似性背后可能存在的文化联系。
一
奥库涅夫文化的所谓“尊”是一种豆形陶器,学术界习惯称为“香炉(Курильница)”。这种器物由底座和托盘两部分组成,器表多饰有戳印纹等简单的纹饰,但亦有“篮纹”、圈点纹等复杂的纹饰[3](图1,1、3、4)。较为特别的是伊特科里2号墓地(Итколь II)出土的一件,器表刻划有三组奥库涅夫文化艺术中常见的神面[4](图1,2),与商周文化饰有饕餮纹的圆腹青铜容器相似,显示了其具有礼器性质。类似的“香炉”在南西伯利亚最早见于阿凡纳谢沃文化,但奥库涅夫文化“香炉”与阿凡纳谢沃文化“香炉”存在较大的不同,即前者在托盘内筑一隔断,将托盘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独立的空间。带有隔断的“香炉”是草原西部洞室墓文化共同体的标志性遗物[5](图1,5、6),因此一般将其作为奥库涅夫文化部分因素源自西方的一个重要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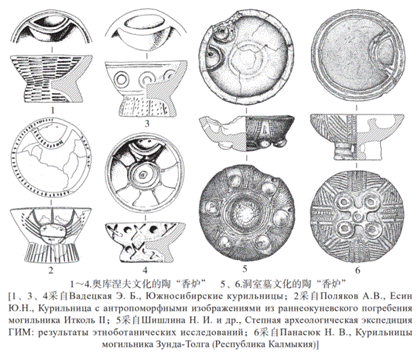
图1 奥库涅夫文化与洞室墓文化的陶“香炉”
奥库涅夫文化和洞室墓文化的“香炉”多出自墓葬内,出土时往往发现器表有用朱砂涂抹的现象,且托盘内常存有植物燃余的灰烬和残渣。2009年,Н.И.希什莉娜(Н. И. Шишлина)团队首次将帖木尔塔3号墓地(Темрта III)等出土的10件洞室墓文化“香炉”内的残留物进行孢粉分析,结果显示“香炉”曾用于焚烧艾蒿(Artemisia)、蔷薇(Rosaceae)、藜(Chenopodiaceae)、紫菀(Asteraceae)、毛茛(Ranunculaceae)、菊苣(Cichoriaceae)等多种科属具有芬芳气味和药用价值的植物[6],从而更加明确了陶“香炉”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除了墓葬中发现有“香炉”的实物以外,奥库涅夫文化的石柱及石碑上亦刻有“香炉”的图像[7],其特点是器表多饰以平行的横线(图2),与叶希河(Есь)出土标本上的“篮纹”极为相似[8](见图1,1)。Ю.Н.叶欣(Ю. Н. Есин)注意到,在奥库涅夫文化石柱和石碑上,“香炉”最常见的位置是人像的头顶处(图3,1~6)。他认为,“香炉”用于焚烧香草、动物脂肪等贡献给神灵的祭品,因此可视作小型便携的祭坛,祭坛置于人像的头顶,目的是为了更接近天空和神灵。值得指出的是,在叶欣看来,标里河口村(пос. Усть-Бюрь)雕像上所表现的是祭坛与车的复合体(见图3,3),并据《吠陀》古经的相关记载认为神车可将祭品送往天庭[9]。在我们看来,标里河口村的“香炉”图像造型与帖木尔塔3号墓地出土的洞室墓文化“香炉”相似(见图1,5),应与神车无关。当然,奥库涅夫文化“香炉”焚烧植物(或包括动物脂肪[10])用于祭祀是毫无疑问的。《诗·大雅·生民》描写祭祀时“取萧祭脂”,郑笺:“取萧草与祭牲之脂爇之于行神之位,馨香既闻”,孔疏:“萧,香蒿也。爇,烧也。言宗庙之祭,以香蒿合黍稷……以合其馨香之气,使神歆飨之,故此亦用萧,取其馨香也”,所涉祭仪与奥库涅夫文化正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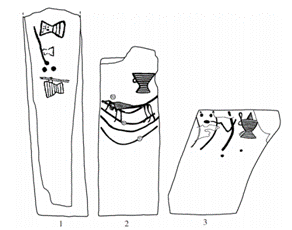
图2 奥库涅夫文化石碑和石柱上的“香炉”图像
(采自Леонтьев Н. В. и др., Изваяния и стелы окун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目前三星堆遗址2号[11]、3号[12]、8号[13]祭祀坑内已出土青铜“顶尊人像”三件(图3,7、8),它们与奥库涅夫文化“顶尊人像”最明显的相似之处在于“顶尊”。许杰先生在论及2号坑出土的“顶尊人像”时指出,头顶容器的人像“可以说明祭祀时青铜容器的一种使用方式”[14]。不难想象,祭祀仪式可能会伴有手持青铜容器的舞蹈动作,其或许可以通过商周时期常见的悬铃青铜容器得到证明(只有晃动时铜铃才能发挥作用)[15]。当然,这在奥库涅夫文化的陶礼器上是不得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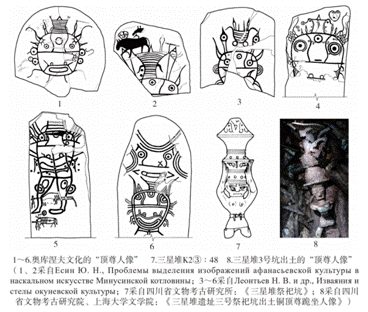
图3 奥库涅夫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顶尊人像”
除了“顶尊”这一显著特征之外,三星堆文化与奥库涅夫文化“顶尊人像”仍有几处可相对比。第一,三星堆遗址8号坑出土“顶尊人像”的觚形尊上有涂朱的现象,该特点与奥库涅夫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陶“香炉”相同。第二,三星堆遗址出土“顶尊人像”分为带獠牙(8号坑)和不带獠牙(2号坑、3号坑)两种。虽然目前发现的3件奥库涅夫文化嘴部相对完整的“顶尊人像”不见獠牙(见图3,1、5、6),其他3件嘴部不完整者是否有獠牙未知(见图3,2~4),但奥库涅夫文化人像可以明显地分为带獠牙(图4,2、4、6)和不带獠牙(图4,3、5)两类[16],且带獠牙者不在少数。因此很有可能奥库涅夫文化的“顶尊人像”也可分为带獠牙和不带獠牙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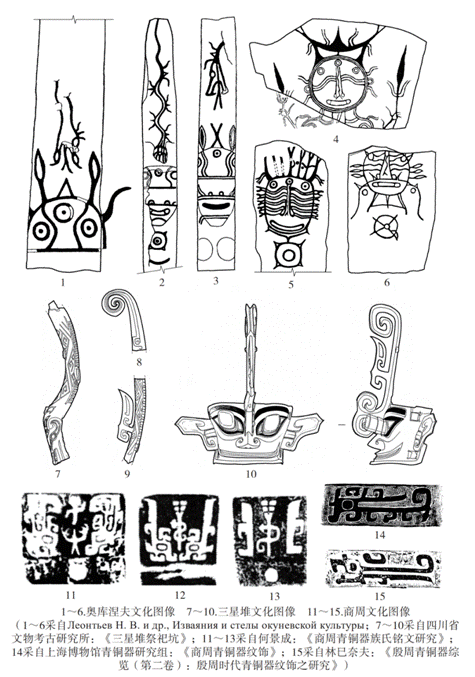
图4 奥库涅夫文化、三星堆文化、商周文化与龙、蛇有关的图像
第三,三星堆遗址2号坑出土可与8号坑“顶尊人像”拼合的双足(K2③:327)呈鸟爪状;在奥库涅夫文化中虽罕见全身人像,且不见鸟爪状足者,但在与奥库涅夫文化联系紧密的卡拉科尔文化中见有鸟爪状足的人像,且其风格特点与奥库涅夫文化常见的人像相同[17]。第四,三星堆遗址“顶尊人像”所顶为中原式青铜礼器,其特点是器表饰有三组饕餮作为主纹,这与伊特科里2号墓地出土的奥库涅夫文化陶“香炉”上的纹饰相似(见图1,2)。关于第四点,需要说明的是,三星堆遗址3号坑、8号坑出土“顶尊人像”的铜尊上,附有立体的头朝下的龙形装饰[18](见图3,8),这不见于奥库涅夫文化的“顶尊人像”,亦不见于奥库涅夫文化的陶“香炉”。但是,龙形动物是奥库涅夫文化石雕上最常见的纹饰之一,且其往往亦位于人像的头顶处,头朝下,作噬人状(见图4,1~3),与三星堆3号坑、8号坑“顶尊人像”的龙纹相似。此外,在奥库涅夫文化当中,亦有小型的龙纹,位于人像的鼻梁处,例如出自切尔诺瓦亚8号墓地(Черновая VIII)、阿斯克斯1号墓地(Верхний Аскиз I)、列别瑞耶1号墓地(Лебяжье I)的标本等,均以上下颚呈球形、吐舌的龙为鼻(见图4,4~6)。我们注意到,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K2②:142、K2②:144铜面具,在额正中的方孔中补铸一勾卷形物(图4,10),其上的刀形纹饰与2号坑出土铜蛇(龙)背部的羽翼几乎完全相同(图4,7~9)。龙简化为翼的情况也见于商周文化,比如何景成先生在研究商周族氏铭文时发现,铭文两侧装饰性的夔龙纹有时简化掉头部[19](图4,11~13),仅剩原在身体之上或在身体之下的羽翼[20](图4,14、15)。据此可以确认,三星堆K2②:142、K2②:144铜面具以蛇(龙)为鼻[21],这与奥库涅夫文化切尔诺瓦亚8号墓地、阿斯克斯1号墓地、列别瑞耶1号墓地人像相同。
二
除了“顶尊人像”之外,还有若干图像可以反映奥库涅夫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艺术的相似之处,兹举数例。第一,列别瑞耶1号墓地所出奥库涅夫文化石碑上雕刻有鬣有角的双龙,二龙相对,共有一个圆球状上颚,可以理解为双龙相对构成一个兽面(图5,2)。类似的龙以及双龙构成兽面的图像亦见于三星堆遗址(图5,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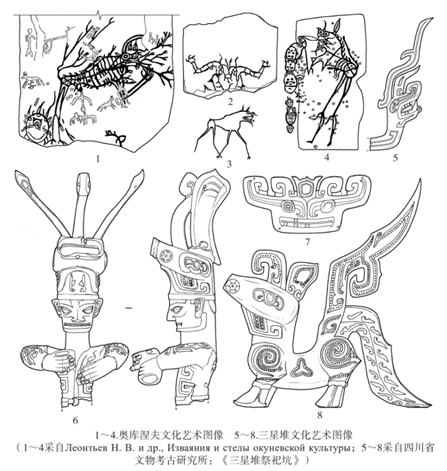
图5 奥库涅夫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艺术图像的对比
第二,奥库涅夫文化石碑上的猛兽,上颚或鼻尖部位通常用圆圈加以表现和强调(图5,1、3、4),三星堆文化的一些神兽亦是如此(图5,6、8)。第三,叶欣注意到,出自阿斯克兹(Аскиз)和苏列克(Сулек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的奥库涅夫文化公牛图像(图6,2、3),其肩部的羽状纹饰与出自布特拉赫特(Бутрахты)的飞鸟图像的羽翼相同(图6,1),并指出在奥库涅夫文化艺术中存在有翼神牛[22]。三星堆文化的神兽,亦以带翼为主要特点(图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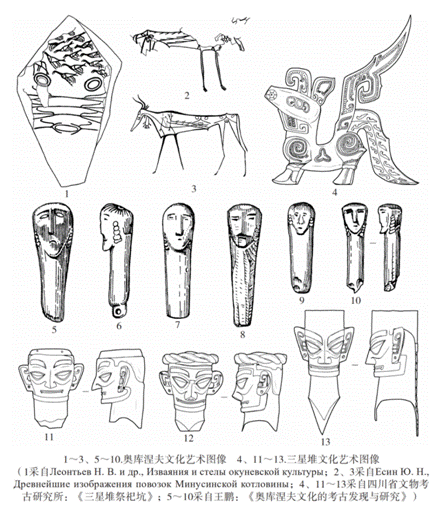
图6 奥库涅夫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艺术图像的对比
第四,奥库涅夫文化常见一种小型滑石人头像[23](图6,5~10),三星堆文化常见青铜人头像(图6,11~13),二者虽存在材质与尺寸的不同,但在整体造型上相似。第五,奥库涅夫文化人像较为显著的特征是弧形阔口(见图4,2~5),这与三星堆人像口部的表现方式相似(见图4,10;图6,12、13)。
三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在奥库涅夫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当中,无论是“顶尊人像”,还是其他艺术图像,均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以往的研究表明,公元前第三、二千纪之交,在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扩散的背景下,南西伯利亚诸考古学文化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表现之一就是奥库涅夫文化与石峁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等一系列艺术图像所表现出的高度相似性[24]。可见,奥库涅夫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艺术的相似并不是偶然的。已有学者注意到,三星堆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艺术联系密切[25],比如三星堆文化的青铜人像、由二动物相对构成的神面,均能在后石家河文化中找到祖形[26](图7)。因此,奥库涅夫文化艺术很有可能是通过后石家河文化,在三星堆文化艺术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当然,经过几百年自身的发展,以及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加之对复杂青铜铸造技术的掌握,三星堆文化创造出的大型青铜造像早已经与之前的石雕和小型玉雕产品不可同日而语了。

图7 后石家河文化与三星推文化艺术图像的对比
奥库涅夫文化艺术不仅在三星堆文化中得到了延续,也在商文化中得到了延续,但后二者的艺术风格并不相同。总体而言,三星堆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艺术的相似性更大,商文化与石峁文化艺术的相似性更大[27]。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测,在奥库涅夫文化艺术南传以及之后的历史过程中,商文化艺术更多地继承了北方的石峁文化传统,三星堆文化艺术更多地继承了南方的后石家河文化传统。此时随着青铜冶铸技术在东亚的崛起,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一道,共同成为了举世无双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正是因为二者在艺术方面拥有共同的基因,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之后,具有两种不同艺术风格的铜器才能“毫不违和”地“无缝对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顶尊人像”便是最好的说明。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虽然已经明确奥库涅夫文化的形成和草原西部人群的东进及其与当地人群的结合有关[28],但奥库涅夫文化艺术起源的问题尚未解决。在我们看来,虽然存在一些西来的成分(比如与牛有关的图像,及其表现出的对牛的驯养和崇拜),但奥库涅夫文化艺术的基底及其反映的信仰体系和宇宙观,无疑是东亚式的(比如带獠牙的神面,以及石柱式的“琮”等)。因此不能排除奥库涅夫文化曾受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影响的可能性。
《考古学集刊》 第30集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